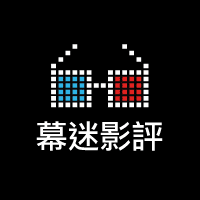前言:論域限縮的幾個藉口
雖然這已是篇遲來的影評,但因為怠惰,我竟尚未拜讀村上春樹和福克納的原作,且只零散地觀覽過李滄東先前的作品,加上已有許多專業評論在前,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我實在無能抽繹出關於三者整合的、系統的、比較的縱論,並且也意識到我對於演技、編劇、音畫、氛圍等影片元素的陳述總不免多餘、拾人牙慧的嫌疑。故基於如上考量,以下我的淺見將只關注《燃燒烈愛》電影中 (一些我自以為重要的) 隱喻所蘊藏的問題意識和可能意涵,時而輔以劇情或相關內容佐證,並期望透過對喻意的澄清和思辨,能為身為觀眾的我們提供一些生產評論的指引。由此,請容我秉持以上的立場和目標,轉入對電影的討論,並在此敬告:本篇有雷。
飢餓與啞劇:問題意識與解法綱領的試提
在影片的前四十分鍾,李滄東以沉穩的節奏鋪敘出鍾秀 (與海美) 的性格、作家夢、對海美的情慾等,並使觀眾能對他所身處的社經境況有初步 (粗糙) 的掌握。同時只消細心點,我們似也能注意到,當中一組基礎的問題意識實已被海美明白地提出:小飢餓 (little hunger) 與大飢餓 (great hunger),其問直陳後分別是:「我如何能溫飽?」以及「我的存在或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前一問題可從單純生理的需求膨脹至對社會現實的實踐疑難,於此影片中新聞播報的青年失業、邊境喊話的政治冷感、城鄉環境的貧富對比等種種再現遂擁有可被統攝地評慮或與其他議題互動的可能依據,乃至呼應李滄東對社會議題一貫的使命性關懷;後一問題則涉及形上的哲思,其何以能交纏前問,成為貫通故事的暗湧,將於後續的書寫中融貫地揭示,但至少此處,若承前問,後問似可延伸出 (但非合併前問) 「於社會現實的各種際遇中人如何自處」此一對後問的解法摸索─是以我們能察覺,前問對諸社會議題所作的綱領性總括,縱然片面卻未必是一種被確定的化約,可說是試圖去指點各議題中的共通,從而引發較普遍或抽象的思維。
現在,先讓我們暫時脫離電影,就此二問題本身略想,則我們似可 (至少是從經驗的認同或現象的直觀中) 得出其間關係的不必然和輕重緩急的排序。所謂不必然,是指兩問各自的產生未必依賴另者的既存,其解決亦同此結構。所謂排序,首要是急,是當生理需求或現實事態極盡迫窘以致難以活命時,對前問的處理將凌駕於後問,且若此況恆常,則後問通常會遭前問吞噬,亦即我存在的意義於我溫飽、得以續存時即刻完備;其次是重,是於非急的處境裏,因後問起而生的尋覓時常會盤踞我們的心智,此時縱使解決前問也難以絲毫地撫平我們尋未果的焦慮,但僅是突圍後問的一絲曙光卻反倒能連帶地大幅舒緩由前問所致的身心壓力。然而所謂舒緩─承前述的不必然─並不即代表前問已解,卻容易使人如此誤認,而正是對此種誤認可能性與上述不必然的 (自我) 意識,使得故事喻意的推展 (乃至觀影時) 總處於某種張力與自反叩問的強迫之中。
繼而返回電影。既然故事所呈現的光景似是那非急之重,是以相較於前問,後問及其方法遂成為內容傾力的所在,但問答的進展於片中實非明朗,特別是當海美談及有關解法的隱喻時。對此需先澄明,雖然前段嘗試區辨前後問的運作方式,然這並不即表示它們絕然分立。實則有一共通早就被點出,亦即兩問皆涉及某種飢餓─而所謂飢餓,我自認可解為慾望的不滿,甚至可視為一種廣泛的宣稱:宣說人的存在狀態、條件抑或普遍人性 (果真有的話) 總立基於某種難以根除且將不斷地迴還反覆的匱乏。是以,當表演吃橘的啞劇,以其食物意象的喻依銜接飢餓其字面的語義時,我們似可猜忖其中或許暗涵對於基本問題意識的回應,而我認為在此,可能的回應有三:(1) 佯裝:知道我沒有橘子,但假想我有橘子;(2) 忘卻:知道或承認我沒有橘子,但遺忘我處於「沒有橘子」的狀態;(3) 追尋:知道我沒有橘子,並設法找到它─乍看之下,第三種解法演不成啞劇。若稍深入探究,則應不難意會:橘子著實地象徵著對前後二問的確切答覆及其實現,啞劇的表演形式則諳合於既定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如何自處的解法問題,三種回應遂是面對答覆有無或根本匱乏的不同解法,其中追尋於此等構架下遂涉及改變現實的企望。然則若承上述,我們似也可領會如是隱喻所窩藏的誤認危險:橘子解饑作為可橫跨二問的共同喻依,任何因渴望它而對它興起的假想或索求,除卻已被真確地貞定為可併解無疑之外,皆易染上將大小飢餓混淆的弊病。是以為免此險,佯裝與追尋於其實踐過程中遂 (至少) 須常保一種自我懷疑或警覺,一種對自身所為的反思的、抽離的認同;而正是如此自反,標識出佯裝策略最重要的特徵─在那裏,自反時常深刻到使人逼臨心智狀態的分裂,因那回返無休的匱乏與獲解的渴望,將使假想的維護,無止盡地遭受對實際解答空缺此一實情的自知,那夢魘般的糾纏。
至此,第一部分可謂告一段落,而如上初步的評估將有助於引導下文細節的詮釋與文末點評。
烈焰、裸舞與三角關係:解法的展演和分判
此部分主要關注三位人物的詮解。我的基本觀點是三位要角的發展分別對應並反映出上述解法的可能實踐與疑慮。無疑地,這表示以下將有頗為繁瑣的點評,但出於立論圓實的自我要求,細節的援引至少能顯示我尚非空穴來風,故若因此導致閱讀的疲勞,在此謹致歉望諒。職是,請容我詳敘如下:
- 班:
優雅多金如蓋茨比─班坐擁超乎必要的物質享受,故無小飢餓的困擾;面對大飢餓時,他似也體悟到一套「自然的道德」作解,其作為也自稱是被動地順應此道德的運行;易言之,在他看來,此道德的構想不止於空中樓閣,更能於現實中完成具體的例現。那何以他還會有讓心中充溢喜悅的渴求?何以他會認為讓骨骼深處響起貝斯聲才是真正地活著?難道上述存在狀態對他而言還不夠完滿?如果「燒塑料棚」僅是班個人的特殊癖好,那麼我們所面對的不也就淪為只是特定個體於既定社會現實中偶然的脫軌,使得前一部分的問題意識與策略試提頓失其普遍的適用性?但倘若我們願意稍微細探其所謂道德,似可意識到:班的犯罪很可能是該思想所蘊含的一個必然結果,進而可從此恢復思想批判的可能。對此我認為,承繼上述的多項前提,癥結不僅在於班的實踐本質上是種掠奪,更在於所謂自然的道德預設了一種無處不至的均衡作為事物發展的目的,且此均衡並非任一個體能單獨地決定─各種事物與個體是否汰除以及如何續存將被一位更高級別的存有者或某種表象下隱密的 (社會) 結構或律則所掌控 ,個體的能動遂受限於發展的順應,是故若僅以此作為存在意義的答覆,則形同未答覆,因我的存在意義如今全受某未知他者的操縱,我成了沒有橘子的傀儡。
[註:班的部分主要延伸自他的兩段臺詞:「我喜歡做菜,是因為能自由地做出自己想的、自己要的東西。還有,更棒的一點是,我能吃了它,就像人類向神奉上祭品那樣。我為自己做好祭品,然後自己把它吃掉。」、「我不做甚麼判斷,只是接受而已,接受它們在等待著被燒的事實。就像雨一樣,下雨了,河水滿溢了,起了洪水,人們就被沖走了,雨做了甚麼判斷嗎?那沒甚麼對錯,只有自然的道德。所謂自然的道德,類似於同時存在......我既在這裡,又在那裏......類似那種,那種均衡。」]
然則何以班仍舊願意奉行這種思想?難道他從未理解如上意蘊?解惑的關鍵在於,自然的道德同時挾帶了一種可能性,亦即只要個體著力在給定的正確方向,個體就有可能久遠地不被自然的發展淘汰,而為說服自己此可實現,遂可得出:如果我已在正確的道路上有所斬獲,我就能以見證非我個體遭汰,來驗證並正當化我先前的實踐─由此,我們或得窺見,班需要藉由定期親摯、參與此道德思想的客體化,在電影中即焚燬無用塑料棚、宰割服貼於他的弱勢女體,來化解他可能偏離「正途」的不安;又更重要的是,唯有那一刻,班的存在意義才能真正地落實,並確認自己彷彿那奧祕的存有或結構般,能促成、甚至形塑均衡,而不再只是纏線的空殼。那一刻,班成了自己的主宰,貝斯聲遂是其骨髓被炙熱的完滿感充盈時的細碎摩擦。
但即便班能如此驗證,其之能為自身主宰終究是一場幻象,蓋有限如我的個體終將難以全然參透、匹配那存有者的意志或結構運作的趨勢,我所能做的仍只是戒懼地臆測以逼近、以求契合「自然」─正是如此的能力差距與實踐的可能不果,不斷地教我意識到我的存在意義仍未著落,乃至它根本不能真正地為我所決定。於是班對自身所為有了抽離的認同,於是在兩∕數次逸樂的聚會中,縱使閒富階級的餘興馬戲節目裏他推出了看似順從地講述世界奇聞的女人,也不禁意識到自己實無能確保她傾心為他所有而心中無有如鍾秀般的特殊存在;不能全心地歡娛而不去意識到這一切可能轉瞬即逝─總之不能擺脫一絲自是的超然、疲倦的漠然。然則如此與現實的隔膜,縱會使班甚至自反地懷疑起自然的道德是否實屬真理,班終將難以棄絕,因這將意味著他必須摧毀支撐他至今的那些幻象,轉而承擔自身存在狀態的崩潰與對大飢餓難題自始至終的內在匱乏。
是以至此,我認為,面對大飢餓,班在佯裝。
- 鍾秀:
身為觀眾,對鍾秀最直截的疑惑或許是:為何他要手刃班?是因愛生妒?還是對階級處境的義憤?此二心緒其動機或皆有摻,可終非要害,因我認為,如是結局實與鍾秀所採取的解題策略深層地相關。欲察見此,我們首先須意識到鍾秀作為電影中乍看與班雲壤相別的人物,除卻性格與階級的迥異,另一重要對立在於鍾秀似乎秉持著未竟的理想,或至少對創作心懷嚮往─雖然不知其理想內容究竟為何,而在影片前段甚至連鍾秀自己也無法說清那嚮往的具體形象,但我們卻能在一組關於日光流變的隱喻中尋獲些蛛絲馬跡。電影裏,無論是午後煦暖的情室、向晚冷清的邊村,抑或是那只能言傳的、異域的大漠夕炎,日光總起著為角色們滌除塵擾乃至喚回某種超脫靈性的作用:於其中海美投射了自己對大飢餓的悸動,而鍾秀則溶入情慾的宣洩並因此瞥見了大小飢餓短瞬的完滿與解脫─日光於此遂不僅是性高潮的延遲或心理學的戀物,而是心嚮的形上願景被柔美的光照視覺化,如此地不可方物以致於我甘願將己身存在的意義寄託於彼。是以,鍾秀的面窗手淫,遂是試圖重返彼刻日照時的離苦,而海美屢以身體、照片、來電的參與 (或中斷) 則使她自己逐漸地被構築成那原初願景當中不可或缺的場景元素,以致當海美失蹤時,該願景即不復可現。至此,我們觸及了一系列關鍵換喻的發動,亦即存在意義─日光─(橘子)─海美:起初,與海美共同生活可能是鍾秀心中對小飢餓預定的解決方案,歷經情慾發酵與多樣事變後海美昇華至與日光相融的境地,同時地落成了鍾秀心中對大飢餓解答的客體化─如此,我們亦別樣地理解了鍾秀急切尋人的肇端:她關係著他存在意義的實現。
繼而我們似可進一步地去思揣:鍾秀的情愛,是否只是將自我的生理慾望與形上匱乏合體地強加於海美,而從未遠離自身地投身於那他連其過往都模糊不憶的她者內在之中?甚或,愛,之於大小飢餓,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成為併解?關此我猶醉中逐月,不敢代以妄詮,但我卻的確由上述的換喻併解捕捉到另一懾人的事實,亦即:對鍾秀既存理想的實踐而言,海美的失蹤 (或死亡) 是有益的。理由可能再簡明不過:因倘若海美被鍾秀尋獲,開始共同生活,然現實條件或將使其陷入未曾意料的物質與相處困難,從而新興的小飢餓將孳生大飢餓的回返,使原先理想的解答地位動搖,且因缺乏具體實踐的動力而凋零─甚至更為直接地,兩人相處後,鍾秀赫然發覺海美已「不復從前」,因此大飢餓依舊懸而未解。是以海美的肉身終須缺席,宣告鍾秀對大飢餓具體答覆的失敗,後方能於近劇末處宛若幽靈地同暖陽忽現於鍾秀的綺夢中,再喚起已然心死的他,那續為理想復仇或以書寫緬懷已逝理想的衝動與渴望。
[註:有相關背景的讀者想必已然發現,通篇文字魯莽地摻雜了 (主要是) 紀傑克和德希達的一些思想。誠然,這種渾淪並置可能已經導致概念的誤用,並且忽略兩位大德理論立場上的分歧;然則之所以仍如此寫作,係出於行文平實的考量─倘若一概運用紀傑克的術語來詮解,恐將使論述旁生枝節且過於艱澀─畢竟意詮「海美是鍾秀的夢中幽靈」比論斷「海美是鍾秀的小客體 a」於字面的理解上要來得平易近人許多。此外,至少就紀傑克而言,當他闡明真實域並非任何形上肯定的超越實體,純粹是一種需嵌於象徵界的空無或絕對否定性,因而涉及象徵化的不可能性與主體的創傷經驗時,似乎能規避德希達對在場形上學的指責,也能呼應缺席、空白主體、幽靈作為象徵債務或某種創傷等想法。然則此中涉及的主體問題及其他爭議的確於文章中未能布置得宜,並且「承認匱乏全然不可能填補,且我就是匱乏」這一進路也將是文中未能顧及處─但關於此等偏重學術的討論,我只能卸責地留與有興趣的讀者繼續鑽研,而未能如論文般嚴謹,對此亦感遺憾。又若當中真有重大失誤,還懇請不吝指教。]
於是我們最終逼近了最初疑惑的樞紐:為何終局的暴行會因之爆發?伴隨故事的發展,鍾秀所深感者不僅是自己與班的物質差距,更是因此物質差距致使己身存在意義實現的可能性衰減,而當班揭露自己的心跡,海美失蹤,且鍾秀所認的證據皆暗示班乃兇手時,鍾秀才獲有藉口來說明對己身存在意義的無能為力實際源於他人邪惡的阻礙,因而全無必要重新省思對大飢餓的舊有解法與答覆。執此,鍾秀劇末的書寫與殘殺遂分別是:絕緣離群於無望且惡業充肆的現世,封閉於一隅,憂鬱於逝者的喪失乃至寄情於彼岸;發覺理想無可能完滿的同時,藐視並毀滅一切施惡的、異端的他者、既存規範權威乃至此世整體─由此,我們得窺探其中自以為是的本質主義心態,尤其後者,甚至可能發展為一種恐怖攻擊的原型,而大小飢餓終究無解。這悲哀的一切皆源於鍾秀策略的偏誤:他因過往偶發的完滿而將大小飢餓結合,並強認他對大飢餓的答案應能統御大小飢餓的解決,即便過程中已現差池亦未能自反。畢竟,特定存在意義的實踐雖可能需要一定現實條件的支援,乃至企圖領導或改善現實的發展,卻不即表示此意義必得固著地統攝、轄制現實條件的任何狀態與變化。
是以至此,我認為,鍾秀在其追尋的過程中混淆了大小飢餓的解決。
- 班與鍾秀:
在轉向海美前,我想先淺談一項我認為頗重要的觀察─班與鍾秀的相似性,並從一則評語切入:《燃燒烈愛》的後一小時藉由女性的犧牲來製造解謎類型─換言之,海美淪為劇情推進的主要工具。倘若我們同意前文對班與鍾秀的分判,則應不難同意此評 (雖非的論) 似已隱約地覺察出其間的聯通:班與鍾秀皆執著於其對大飢餓答覆的客體化占有,以此圖獲對己身存在意義的固著落定─正是於此等意義上,海美被他們符號化,變成指涉其各自存在意義的載體或容器,她自身的能動與發展可能早在悲劇幕啟前就已於三者相處中被單方面暴力地否定─「妳怎麼能那麼輕鬆地脫衣服,當著男人的面?妓女才會那麼脫衣服。」鍾秀那涵蓋某種禁制的怨懟遂是上述所言的映現。至於另一聯通,我認為在於,當鍾秀因實現無望而付諸閉關與凶行時,其抉擇的立基之一承上述在於假定他人之惡─這難道不也可能是一受虐的幻象,藉此讓自己避免再度正視對大飢餓的匱乏與自身赤裸裸的無能,因而是一種更為迂迴的佯裝 (亦即知道我無法有橘子,卻假想我可以有橘子)?且為不斷確認他人之惡,鍾秀是否可能陷入雷同於班的輪迴?果真如此,那麼劇末的烈焰將不僅是底層青年的怒吼,或是讓富豪的骨頭如願以償地燒得劈啪響的嘲諷,更隱含對佯裝模式薪火傳承的幽慮。 我們因此不忍卒睹:原來農家刀具和名牌化妝品,所為其實如出一轍;義憤填膺的鍾秀與望湖遐思的班,其對大飢餓的解法選擇,差別可能在於有沒有一臺保時捷,僅此而已─
佯裝或許亦是那曾經激奮過、惘然過的追尋。
[註:烈焰所涉的另一隱喻,於文中,我亦未能及時談論:當海美最後與班離開農村時,鍾秀意識到他的話語傷害了海美,可能因此完全失去她─下一幕,於鍾秀的夢中,童年遭父親逼迫火燒離家母親衣物的回憶和班所論縱火的想像竟被混雜成團。母親、海美、父親和班彼此間能產生怎樣的聯繫和解讀呢?]
- 海美:
我必須自首,將忘卻歸於海美,並非因觀影中已然洞察任何有力的證據,而僅出於這是她的灼見─故對此我只能假設:電影裏海美的言談舉止至少能為我們輕揭起此謎樣解法的羅紗一角。
縱然,忘卻仍可蔓生豐繁的歧譯,且每種解讀都將可能導向彼此截然相異的判定。 若單就前文的定義而言,我們似可將忘卻再細分作二:(2-1) 知道但遺忘;(2-2) 承認但遺忘。若為前者,則幾與佯裝無異,甚將因缺乏自反或逃避形上哲思,使大飢餓懸擱蒙塵─基此復將大小飢餓合併,則似可得出「遺忘社會問題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此種顯見的謬論。若為後者,其承認卻與前者的知道有別,涉及自認己身面對難題時的根本匱乏,乃至如是匱乏的填補不可能;而其遺忘,於我的詮解下,乃旨在對特定答覆、解法及其追求的破執─那將是一種對曾受隱蔽的多重可能性的發掘,以及對所假定對象喪失的不再悵然─是以忘卻將不會涉及割捨或迴避大小飢餓,而是一種重新看待大小飢餓的基進方式,於是與佯裝產生了重大的區別。此種忘卻所能達致的境界,回顧隱喻本身,即是啞劇的演成─若復承繼前述我們對啞劇形式的解讀,那此境界似是一種涉及美感的經驗、一種對現實條件下己身存在狀態的再詮。於是我們得見:海美仍舊有其對大小飢餓的感觸與困惑,有情慾、意志和因之產生的行動;她能夠透過身體自主律動的介入,將彼刻邊境的肅殺、蕭索乃至百無聊賴,轉譯成那些早被長久對立與冷感所埋葬的吉光片羽;她的裸舞則為貧富男性演示了對大飢餓的答覆有共同渴求的可能,並由此孕育出各異的實踐。執是,她才能成為故事中唯一能自在遊蕩、穿梭、沉浸於各階層的體驗者,於階級間鑲嵌能翻越物質圍欄以促成跨層改變的契機─正是於此意義上,我才能說,海美可能走得比誰都遠。
[註:忘卻究竟是存有的遺忘、本源缺席的遺忘、喪失的喪失,乃至是覺無自性並「空空」,抑或是其他解讀?這一問題,於此,亦謹交予有興趣的讀者自行詮解。]
然而,實際的情況卻非如此分明立判。我們同樣亦須意識到那些靈光之為幻象的可能,亦即這種境界其實根本地奠基於一定的物質條件:去非洲旅遊,要錢;聚會中再詮異族祈舞,要喝過紅酒;夜店熱舞 ,要滿場轟鳴的音響和撩亂的色光;最後於邊境裸舞,要犯法的大麻─後三者尤為要,因即便─承上述─存在意義的實現大多需要物質的支援,但那些是海美於彼方漠土頓悟其形上願景後的再詮,卻似必須處於意識迷糊中才能通達,且皆由班供應其物質條件。我因此不禁心生疑惑:莫非此等忘卻,終究需要中產階級以上的物資才能達成,因此海美的沉浸又可能將變相地落回 (2-1) 的遺忘?此外,從故事發展以觀,我們同樣未能得見:此境界達成後如何能生成改變?─我的意思是,縱然海美的忘卻仍舊渴求去解決大飢餓,故境界達成後的實踐動力問題似有跡可循;縱然班與鍾秀皆因海美而被觸發行動,但承上述詮釋,班與鍾秀實未被改變,其所為仍僅是原先自我的延伸,而海美本身卻似未有具體改變的行動而停滯於表演啞劇。因此上述的問題遂真正是:當多重可能性展演於我眼前時,我如何做出抉擇?
如今,身為觀眾與讀者的你我,想必也同樣地感受到此問題的迫切性。可是很不幸地,走筆至此,問題早已變得更加棘手:當三人的抉擇皆以失敗告終,當我們發現所有可行的方向皆會導向窒礙或崩壞,或每種看似可能的解法都讓我們察覺大飢餓解決的「不∕可能性」 時,我們如何能做出抉擇?
於是乎,我們遭逢了不∕可能性纏繞的困境,大飢餓之謎於焉回歸。
不過,對此我認為倒不必畏縮頹喪,因為新可能的幽光其實亦早已於困難加劇時偶現其影跡。
[註:此處所謂「不∕可能性」,未必指涉實然或模態上的不可能,反可說是:當我們處理難題解決的無限可能性時,我們發現既存的每種可能道路皆窒礙難成,而我們的理性計算或邏輯推演能力卻早已癱瘓,是故無能擇定─此時為解決難題,遂必須突破我們既有的觀點視域、律則規範或認識範疇來探索新可能。如是,我們才能說,透過對「不∕可能性」的意識,那被我們突顯為困境的難題才首度被認真地對待,難題被解決的可能性方有可能浮現─執是,德希達認為,此中纔真正地涉及倫理的行動。]
[註:夜店場景的那顆鏡頭,我認為極度凝鍊地統整了我文中的觀點:當中班只是旁觀海美於舞池中熱舞,而鍾秀卻逆著人群攢動的方向,選擇離開那縱欲享樂卻只有人造光影的地方,回家。]
夢中幽靈與世界如謎:書寫虛實間解法的可能性
現在,且讓我們重新審視海美失蹤後回返於鍾秀夢中的橋段。就先前的脈絡而言,海美的入夢只不過是鍾秀原初形上願景失落所滋長的鄉愁,於此解讀下,海美猶只是鍾秀的自我投射。然而,我們不能遺忘:電影至今困擾著我們的基本問題意識,是由海美提出的─正是此一事實使我們或可探得一條此前隱沒於煙靄中的羊腸小徑,而一組新的換喻系列將是鋪路的碎石:存在意義難題─飢餓─海美。秉此換喻,海美的回返遂可詮釋為:當鍾秀意識到一臺保時捷的差別並不純粹是一受虐的幻象,而是一真確發生的社會結構性現象,且此種現象將導致多數社會成員其存在意義的實現遭受極大的阻撓,但對之卻無能改變、準備放棄時,那大飢餓疑難的沉默回歸。海美於是以其默然的魂牽夢縈,逼使著鍾秀意識到自己不僅糟蹋了她曾經賜予的安樂圖景,最終更因自己的暴力和無能,犧牲了她。歉疚與承認遂由衷薰起:歉疚將驅使鍾秀回應那關切他自身內在的、卻早已不為他所掌控且不屬於他能力範圍內的困境─那既在他自我之內又在他自我之外、既源出於我又相異於我的他者之謎;承認將是認定從前對大飢餓自我中心答覆的災難與不應復襲,因而必須另尋新興且不蹈前轍的可能解答。海美於是蛻變成討債的夢中幽靈,教鍾秀負起不可能克盡的償還責任,並使他覆寫了大飢餓的問句─原來從來就不是我的存在意義為何的問題,而是我如何與海美共享甚麼存在意義的問題,乃至我如何與他人、已逝的海美和大飢餓本身共享甚麼 (存在意義) 的問題。於是乎我們見證了立場的翻轉:以往鍾秀試圖將海美收編於其自我的符號編碼中,如今海美乃至眾多他人卻永遠地行跡於鍾秀所認定的自我邊界上,持續地擾動並質詢著他─質言之,鍾秀的大飢餓答覆將不可能全然確定,其解決與否亦將全然取決於他者不∕可能的未來首肯。如此,一種回應他者的無限 (可能) 責任誕生了。
然後我們來到了早先提及、如今將成全片至要關鍵的一景:鍾秀由蜷縮地背對窗牖,轉向面對窗外早已陰霾、日光不復明媚的窗景;他於公寓窗框內打字,寫起小說,寓外則是一片晦暗叢集的城市。書寫─承此脈絡─遂不再是自我封閉,而可以是一種對他者的敞開,一種肩負起社會使命,或描繪、實驗願景如何可能的任重道遠,一如電影本身。大小飢餓合併解法的可能於是透出了光:面對小飢餓鍾秀或可憑書寫獲得溫飽,底層困頓的紓解也可因書寫而為社群所關懷,並意識其之為困境;面對大飢餓,書寫亦尋獲一種根本變異原先觀念的問題意識與解法可能,同時亦因此種突變,使得它既是忘卻前限,又是浪漫地追尋將臨的不∕可能的願景。
基此合併的力量,我們遂於劇末目覩了鍾秀施展出遠比海美的啞劇更強勁的遺忘,並對其可能潛存的、超乎任何溢血殺戮的激進暴力,驚鴻一瞥。蓋書寫橋段使我們不禁質疑起劇情的「虛實」─舉凡神隱貓、幼時的嫌惡與水井、無名電話、母親借錢、海美被殺、班被殺等那些眾多影評反覆強調的、連李滄東於受訪時亦玩味指出的有無擺盪,乃至對整部電影是否僅為鍾秀創作內容的存疑,都可能使電影中對社會現實的一些再現、批判,以及既存的詮釋和論斷,其真偽懸置;換言之,這股編導、剪輯和觀眾後設的自反匯流,之於本文,終將可能顛覆前文所有陳述。然則如是懸置是否意味著對評斷與責任的無法承擔與迴避?恰好相反,那反而是對所有可能產生的問題與論斷的高度重視。於此,電影的內容與形式變得既崩解又繫合,(想要理解的) 觀眾將被迫拔除自己所有對電影理解的前見與設限,同時又被迫全盤再詮、並於詮後再被迫參與三人行動的抉擇以生評斷,如此循環反覆─相較於電影中的謀殺,後者僅是結果的暴力,兇手仍是根基於自己的準則與價值觀行事,而從來不曾踰越對自身存在狀態的畫限。是以,當電影與觀眾的關係能雷同於世界與鍾秀者,並經由觀影,觀眾得以介入故事的安排,我們似能對鍾秀的感慨萌生更刻骨的同理:世界如謎,但縱使其中困境重重,難解無定詮,我們仍盼望由不∕可能邁向可能,而書寫於此似是其中的可能之一。彼時理解電影、理解自我、理解世界皆將涉及回應他者的責任,如此則疑難將無可避免,而身為盡責的觀眾,對於那些盤根錯節的謎題和隱喻,遂需要反覆觀影、反覆再詮─
是以,班的一項建議著實真確無誤─關於隱喻的問題,我們得再去問問鍾秀。
檢討與再思:困境的延續 ?
倘若以上的論調能被同意,則我想應能產出以下對此部電影整體的點評:
1. 電影後半淪為反傳統但不甚出色的懸疑類型?未必。縱然後一小時稍嫌拖沓,但此論的產生似必須先認定電影後半只是懸疑片;而若能同意上論,則將明瞭:電影後半演示兩種解法如何衍生缺陷,並高度自覺地處理了貫串全片的形上問題,並為此懸置推理求真相的觀影快感─(至少在此意義上) 是謂反傳統。是故未必有從形上問題衰退的跡象。
2. 電影後半女性淪為劇情推進的工具?未必。承上述,雖然對班與鍾秀而言海美的消失是推進,但此推進不僅在於劇情經營,更涉及形上問題的處理,且我們亦不能否認電影前半也呈現了海美的意志、情慾、思考等,因而甚可說電影中的女性不只是功能性角色。然而,可商榷處在於,若電影─如導演自述─旨在刻畫現代青年的矛盾,並因此為其改編添加階級背景的人設,復加考量上述對忘卻解法的物質基礎顧慮,則我們似可質疑:海美的沉浸與其被輕描淡寫的沮喪 (遭斥為妓女) 和寂寞是否真能反映現代女性青年的困頓經驗?若不能反映,那電影是否僅剩 (至少是) 男性青年的形跡與慾望投射?
3. 電影末尾的謀殺是未成功的階級反撲?未必。承前文,我們尚需重視書寫所開啟的詮釋的可能性。假使鍾秀的書寫植基於回應他者,同時亦是一種高度自覺的創作,那麼其書寫謀殺不正是透過將底層青年個體的無能改變突顯為一種社會現實中無解的困境,而教其 (同樣有高度自反的) 讀者去思考真正能解決困境的可能性─簡言之,一種未作定論、拋磚引玉的曲折回應?
4. 電影不過是令人失望的社會批判?未必。因縱然三位角色對大飢餓的解法實際不必然與其所處的階級位置相關,是以似乎未能以其個體普遍地概括階級中的群體,但三位角色所對應的大飢餓解法卻有一定的普遍適用性 (對此希望我於前文已達成使人信服的揭示)。是以當三位角色試圖實踐其大飢餓或併解大小飢餓時,小飢餓中的議題即無可避免地被觸及─其實踐運作的成敗,亦關係到小飢餓議題如何被處置。是以我會認為,電影或許並未正面地處理階級的具體議題,然而卻涉及一更抽象的、可跨階級的思想批判,其中包含如何看待社會問題與存在意義問題的方法論。
5. 電影裏的階級是缺乏群眾能動性的薄弱再現,或說它忽略考量群體如何一同參與解決大小飢餓的可能?可能如此。然回應他者的責任似可作為後續對此延伸思考的依據;且細究起來,階級群眾仍以既在場又不在場、既於電影域內又於域外的幽靈姿態懸宕於背景裏,蜷曲於那片晦暗城市樓房中各自的蝸居裏,而不為我們所全見。身為觀眾群體的我們因而被迫與鍾秀一同直面此一不∕可能性。
至於以下,則是對前文諸隱喻詮釋的詰難─當中將涉及一些尚不∕可能有解的困境:
1. 於前文中,我似乎認為電影中對大飢餓解法的固著是危險的。然則如是詮釋與對大飢餓的看法本身似亦可能涉及以下固著:(1) 可能性與固著此一二元對立的固著;(2) 認為電影由一組問題意識統領全局的固著;(3) 欲將電影所有流轉的音畫落定地賦予深層意義,或說表象與真理此一二元對立的固著。對此,書寫與電影的反覆再詮又能如何為我們另闢旋踵的餘地?
2. 於前文中,我似乎認為回應他者的書寫是電影中大飢餓解困的可能出路。然則如此書寫似亦有其重大疑慮:(1) 我們先前對佯裝的批判正是立基於某未知他者對人的全然操縱,但回應他者於此面向不亦有類似之處,它因此何以能避免落入佯裝的窠臼?(2) 電影中書寫的起始似仍源於對所處社會位置的基礎認同 (即承認我在此位置),由以生起對當中所受境遇的反抗,如此則回應非處於與我相同位置的他者將如何可能?若可能則原先改變、反抗的使命感如何續航?(3) 若書寫與詮解總難以避免困境的遭遇,因此必須反覆施作,然則由眾多他者所不斷衍生的各異實踐如何能形塑社群為共體?(4) 當書寫展現為必須不斷地被反覆實踐與詮解時,不正反面地宣說其背後並無任何寫作原意的固著,因而也是一種詮釋立場的固著?
若諸此疑難果真無解,則困境依舊,大飢餓回歸。
至此文章將暫時告終,而我終究識淺,故行文必有誤陋偏狹以及馬虎之處,若能受不吝賜教,當感激不盡。最後在此誠摯地感謝您的耐心閱讀,並希望這篇文章至少能讓您我對電影的投入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關於這篇文章的產出,有三篇網路上的影評對我有所啟發,於此羅列以表謝意:
BIOS Monthly:2018 坎城現場|《燃燒烈愛》:李滄東與村上春樹的矛盾碰撞
https://www.biosmonthly.com/issue_topic/9613
《放映週報》第 626 期焦點影評:從〈燒掉柴房〉到《燃燒烈愛》:影像改編的再創作
https://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2198
豆瓣影評:李滄東《燃燒》:世界靜默如謎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428123/
故事劇情:9
氣氛營造:9
演技表現:8
題材鮮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