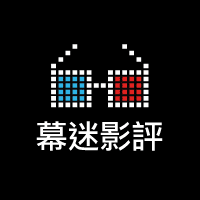《大象席地而坐》(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是已故導演胡波生前執導的最後一部作品,於2018年11月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這是一部極輕卻也極重的作品,觀影者看著電影裡頭的人物被「生活」這個巨大殘酷的碎紙機分解、揉碎,而零零落落飄散的紙屑就是他們,不對,倒不如說是我們,因為他們就存於我們裡頭。故事圍繞在中國不同年齡層的男女,在一天中經歷各樣的衝突和反覆的生存性憂慮後,毅然搭上車,前往滿洲里看那頭成天坐在地上的大象是否存在。
電影很明顯地籠罩在一片濃重而化不開的「灰」中,不管是中國的霧霾、殘破的工業廢城,或是人們心理上的壓抑和絕望,一切都被壓縮在那樣的真空狀態中。導演胡波幾乎是用長鏡頭串聯起整部電影的,每個人物的故事線就是那樣緩慢地行進著,透過長鏡頭類似於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去窺探每段無語的對白、每個無聲的控訴和吶喊。

電影中時常出現的畫面是鏡頭跟隨著人物的後背不斷移動,而在畫面中,人物以外的景物都是模糊的。在我看來,人物像是在一片由混沌的灰白構成的荒蕪中禹禹獨行。一幕幕畫面中極淺的景深其實使我看得特別無助,這也讓我意識到,在這部作品中,觀影者並不是站在高處(在普遍的觀影經驗裡,許多電影的觀眾會比故事中的人物更早洞悉、掌握許多事和情況),許多物事也會比人物慢幾拍才領悟,而我們始終與他們保持著一段距離。這樣的淺景深同時也隔絕了畫面中人物與環境的連結,若說他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也顯得太過武斷,但他們確實像是在自說自話,偶爾穿插著一些斷斷續續的對白。不過,他們卻也不等著別人的應答。
到了後半部,劇中人物被不斷壓抑的內在終於噴發,真空的包裝終於漏出一點縫。不同於前半部,角色們的表達、言語動作間透露出的淡漠以及毫不在意,後半部的情感張力強烈引起了觀影者的共鳴。韋布面臨災禍後與林凱的對立(橋上咆哮的片段令人印象深刻)、黃玲與她母親歇斯底里的爭執、于城對好友母親的坦白、王金與孫女私下的出走,都是對生活的孤寂、無奈與貧窮所做的逃脫,或者是反抗。每個人都將期盼寄託於滿洲里那頭席地而坐的大象,卻誰也不能肯確牠是否真的在那兒。
其中一段台詞是這樣說的,「我告訴你最好的狀況,就是你站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那邊的那個地方。你想著那邊一定比這裡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決好這的問題。」換一個角度來看,《大象席地而坐》傳達的概念並不如其表面上看來的消極,反而能從中品出積極對於世界、對於自身做出改變的意念。我們可以對一切生活感到疲倦、無奈,我們可以嚮往著別處、另一種更好更理想的生活,但當我們回到原點,依舊必須面對、甚至解決存在於生活中的種種課題。

最忘不得的是于城在殘壁殘垣上,與韋布的對話,以及對好友母親的坦白。「如果你現在在一個高樓陽台上,會想什麼?」「不想。我還能怎麼辦。」看著于城瞭望著失焦的灰幕,顫抖的雙眼對映了他飽受掙扎的理智和感情,明明是個看誰都不順眼的人,卻還是在此刻卸下滿身盔甲、留了一身赤裸。
電影的最後一幕是我最喜歡的一顆鏡頭。畫面中的大巴停在路旁,乘客稀疏地下車走動,人們在車前踢著毽子,人影在唯一的光源照射下被拉的長長的。這時,遠處突然傳出一聲大象的嘶鳴,人們都被這叫聲吸引而停下了動作,接著,又是一聲嘶鳴。這聲鳴叫劃破了深深灰暗,而那真是滿洲里的大象嗎?我們不得而知。至少,牠成為在大巴上等待著另一段旅程、另一個開始的人物們的嚮往與希冀。而人生是一片荒原,有時,僅僅是希望著就足夠了。
故事劇情:8
氣氛營造:9
演技表現:9
題材鮮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