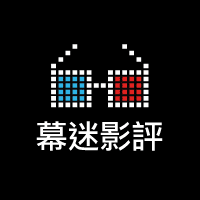一眨眼又快兩個月沒更新了,在此向本部落格為數不多的讀者(有人嗎?)深深一鞠躬。
會這麼久沒更新最主要是因為最近都在趕金馬影展,閒暇時間幾乎都泡在電影院,而且看得太多反而不知道要從何寫起,所以又這樣一天拖過一天,直到金馬獎頒獎典禮這一晚。
每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可以算是我行事曆上的一項重要行程,通常這一晚我一定會排出空檔守在電視機前面─沒辦法,誰叫我是「追星族」。不過今年頒獎典禮因為大象我一整天12個小時都在電影馬拉松,早上先看164分鐘的《柳川堀割物語》(1987)下午再接著看507分鐘的《死靈魂》(2018),等走出電影院都已經晚上11點半,頒獎典禮也接近尾聲了。
因為對《死靈魂》導演王兵的作品認識不算透徹,所以本來不準備寫《死靈魂》的心得。但當天晚上11點半從電影院出來,打開手機社群軟體,某些消息一直刷我的塗鴉牆,才知道在我看電影的同時,金馬獎頒獎典禮地震了。
可能因為不是第一時間看到現場畫面,所以在「台灣獨立」、「中國台灣」的網路激戰當中,我很反常的沒有絲毫激動(當然也有可能是才剛剛看完了長達8小時又27分鐘的人間慘劇,心情還沒有平復過來吧)。只是冥冥之中覺得似乎有點巧合的在我了解「一點都不能少」或者「一點都不想多」的議題之前,我先重新回顧了一段關於中國在1960年至少有2千萬人活活餓死的歷史。
《死靈魂》是一部紀錄片。影片主角是大約三千名來自中國甘肅省附近的知識分子,他們多數是在中共於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中打為右派分子(或反革命或壞分子),並被送進位於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一個勞教農場-「夾邊溝農場」。3年後,這三千名不是囚犯更似囚犯的人們只剩下大約五百人還活著,其他人則是餓死或被折磨至死—《死靈魂》正是這些死者的紀錄片。
死掉的人怎麼會是影片的主角呢?
2005年,導演王兵正根據中國作家楊顯惠的紀實小說《夾邊溝記事》、《告別夾邊溝》著手準備拍攝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為了補充資料,他自2005至2007年這3年間,使用一台小的數位相機,訪問了上百位「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多數的他們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長者了),並以此為據,在2007年完成一部2個半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以及在2010年完成前述的劇情長片《夾邊溝》。但後來王兵在倖存者反覆口述挨餓的回憶中發現,主角應該是那些死去的靈魂,他說『就在這一刻,它被喚醒了,被影片喚醒了,被記憶者喚醒了。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死靈魂》 裡的14位受訪長者,每一位都有非常充裕的時間向導演/觀眾介紹他們自己的生平、他們去夾邊溝的過程以及在夾邊溝的生活。這當中有人是公務員、有人是黨員、有人是基督徒、有人是在「雙百政策」跳坑(請看最下面的反右運動解釋)。他們到了夾邊溝之後,有人當伙夫、有人養兔子,多數的人則是在硬得跟鐵一樣的土地上日夜勞作試圖種植農作物。然後因為錯誤的農場政策以及國家大躍進運動的失敗,這些人開始挨餓,糧食配給的數量越來越少,最後一人一天只有250公克的食物可以吃(大約是2個半的御飯糰),與塞牙縫的食物分量相反的則是高度體力勞作,種不出東西也得種—因為這是一處勞教農場—否則農場幹部無法向領導交代。
時間似乎沖淡了一些悲哀、一些恐懼,影片中多數的長者都以輕鬆的態度向導演/觀眾訴說那地獄般的時空:挨餓、吃草籽、腹脹、便祕、互挖大便;偷食物、吃老鼠、吃人肉、吃糞、吃嘔吐物;浮腫、消瘦、死亡、棄屍。然而每當講到關鍵時刻,他們彷彿又變身為那個漫天黃土的窯洞裡餓得神志不清的自己:他的語調突然高昂起來、身體不由自主搬演起那時的動作、甚至面帶微笑講述別人的死亡。此刻我們會覺得時間只是腐蝕他們的肉體,他們的精神與記憶一直活在那痛苦的一刻。
而時間也腐蝕了亡者的肉體,那超過兩千位莫名死去的人們,被棉被一綑就往空地丟去,只以一抔黃土為墓。50年後,他們的殘屍枯骨散落在夾邊溝的荒野上,殘缺的顱骨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如果身體不能入土為安,不知道他們的魂魄有沒有重歸故里?

(圖片來源:端傳媒)艾曉明《夾邊溝祭事》 )
《死靈魂》 電影沒有告訴觀眾整個事件的歷史、社會背景,我想或許是因為導演認為「對我來說,更著迷的是那些躺在戈壁灘下面的人的故事。可能我們通過別人的記憶,只能恢復他們一點點的信息,儘管是一點點,我都覺得非常神秘,好像你真正影片所要講的那種感覺」
但這些死靈魂見證的不只是「夾邊溝慘案」,還有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大飢荒,那是前文所說的「至少2千萬人活活餓死的歷史」。(如果你對這段歷史有興趣,我下文會補充,或許你可以直接往下拉)
這些早已過去的事實,在頒獎典禮上說出「台灣獨立」的最佳紀錄片得主導演傅榆可能不知道,那麼說出「中國台灣」的上屆最佳男主角涂門知道嗎?說出「兩岸一家親」的本屆最佳男主角徐峥知道嗎?那些瘋狂轉發共青團「一點都不能少」的明星們知道嗎?
我無意在此批評這些明星、演員,就像我也不希望有人批評傅榆害了金馬獎一樣。我不能要求別人勇敢,只是這個世界總是需要一些勇敢的、莽撞的、沒有禮貌的人,否則夾邊溝的歷史有誰會記得?否則誰能討論火燒島?
說來有點諷刺,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清算、帽子、批鬥,除了小學時期台視連續劇《芙蓉鎮》給我一點懵懵懂懂的印象外,我最先是從張藝謀導演的《活著》(1994) 還有陳凱歌的霸王別姬(1993)開始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如今這兩位兩位國際大導演都飛往青天了,徒留我們這些平凡的低端人口在墳墓前感傷。
行文至此,我想更正前兩段所言「這些早已過去的事實」這句話,因為「勞動改造」或者「勞動教育」它從來沒有成為過去。2013年,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血腥殘酷還歷歷在目『被用子宮擴張器插進嘴裡強行灌食數月,被用電警棍放電來擊打乳房和生殖器官,被電警棍插進陰道裡電擊,被往陰道裡灌辣椒面等酷刑』,且中國政府已於2013年底正式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未料2018年所謂的「再教育營」又悄悄包圍西藏的維吾爾族人,媒體報導:『聯合國估計,新疆大概有1百萬維吾爾人被關入再教育營內,每天接受洗腦教育。得早上5點起床要學很多東西,白天要唱歌唱個2小時,有時候會3或4小時,要欣賞歌頌習近平跟共產黨的電影,進行思想再改造。』
如今這麼大的世界,這麼多人想跟中國當朋友,沒有人能阻止這麼殘忍的事情。
或許你會說 這是中國的內政,那我們來談談兩岸關係。
我也很捨不得躺著中槍的李安導演。
但半個世紀來,台灣與中國活在一個兩邊都不是事實的夢裡。台灣(好吧~如果你要說中華民國)有自己的國號、國歌、元首,但這個世界不承認我們。
中國說一點都不能少,但(至少在中國武力犯台之前)台灣不可能唱他們的國歌、台灣人民不可能認定習近平是元首。(即便是黃安、張安樂、劉樂研之流也不可能輕易變成中國公民)。
這個兩邊夢一場的飄渺,李安導演那一代無法解決,我這一代可能也無法解決,難道我們要阻止我們的下一代(試著去)解決嗎?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說自己處在時代的矛盾中呢?
【關於那段歷史】
反右:
中國的「反右運動」始於 1957年,不過事情不是從「反右」開始。1956年,蘇聯前最高領導人也是獨裁者史達林過世3年後,他的接班人赫魯雪夫突然對史達林以及史達林主義進行批評,他強烈抨擊史達林清除異己和驅逐少數族裔的罪行,猛烈抨擊他農業政策帶來的災難,還攻擊他軍事指揮上的無能 (來源:)。一直以史達林為標竿的毛澤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他擔心如果有赫魯雪夫這種「修正主義之輩」蟄伏在身邊,他會落得跟史達林一樣被鞭屍的命運。於是毛澤東想出了讓文化界「百花齊放」、讓科學界「百家爭鳴」的點子,以及喊出「大鳴大放」的口號,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以為如今共產黨已經容許他們可以表達不滿,結果這只是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尤其是毛澤東發現知識分子批判的箭靶已經到他本人身上後,他便下令根據這些意見,把幾十萬人設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秋後算帳,這一年約有30萬名的知識分子的人生斷送在這場反右運動。
饑荒:
在鬥死了大約一百萬名地主之後,有一段時間中共允許農民在合作社(共有共耕)的制度下,保有不超過5%的自有地,這自有地讓農民很開心,因為他們可以得到公社共同勞動成果以外的報酬,但這情況看在毛澤東眼裡則擔心新一代的富農階級又將崛起,於是1958年夏天,所有的私有化制度都取消,合作社整併後,變成了(我們熟知的)「人民公社」。這是三年饑荒悲劇的開始,錯誤的農業政策(不懂農務的幹部瞎指揮)、大約一百萬座的土法煉鋼廠(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糧食產量大減,卻只能煉出大量的廢鐵)、糧食產量虛報(反右運動讓有專業知識的人不敢講實話)、白癡至極的打麻雀運動(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都是造成這場餓死至少兩千萬人最多四千萬人大饑荒的原因。1957年,中國死亡人口年齡的中間值是17.6歲,到了1963年下降到9歲,也就是說,這餓死的兩千萬至四千萬人(已經是整個台灣)有一半以上是小朋友。
夾邊溝因為是「農場」,在全國糧食不足的狀況下,中央政府認為「農場」應該要自給自足(完全不考慮沙漠的天氣與地質),這就是《死靈魂》發生的時空背景。
(關於金馬獎的定位以及他與中國電影的關係,今天已累改日再戰)。
故事劇情:9
氣氛營造:9
演技表現:9
題材鮮度:9